中國留學生的體育生態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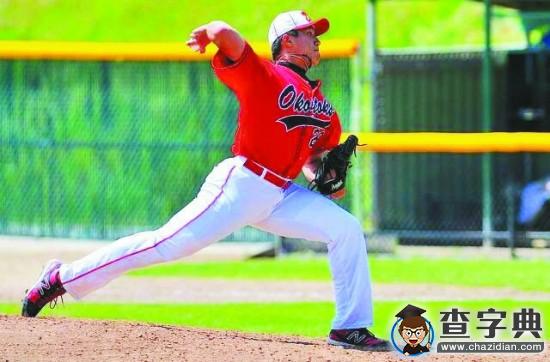
為圓職業棒球夢,從事棒球運動14年的劉源選擇出國留學,圖為在他加拿大參加棒球比賽。
體育不僅意味著強身健體、實現夢想,還是融入當地社會最好的快捷通道——回美國的前一天,劉源忙著在清華大學的棒球場攢了一場比賽,陸陸續續來了近20個男孩兒,“全是一起打棒球長大的哥們兒,現在都各奔東西了。”他坐在場下,看見有球飛出球場便跑去撿,看見誰在場上待得太久便招呼:“換換人,大家都上場打打”。
有時看到場上屢屢出現壞球,他也手癢得想試試,但一想到這個場地是以800元一小時租的,他便會按捺住沖動,“我的目的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打打球,聊聊往事,讓他們多打會兒吧,明天回去,我又要過看見場地就‘想吐’的日子了”。
第二天,他在朋友圈寫下“走了”兩個字,然后附上一首《20歲的眼淚》:“是20歲的男人就會離開,能夠離開所有柔情的牽絆,是20歲的男人就不該哭泣,因為我們的夢想在他方……”
他一直努力想當最后一個走出力量房的人,可總是會有隊友和他一樣加練到很晚才離開,“他們對棒球的執著,那種為了夢想的付出打動了我,相信努力是不會說謊的。”
參加高水平比賽并在比賽中被大聯盟的球探相中,這是劉源成為一名職業棒球運動員最好的方式。從小打棒球并把加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視作終極愿望,劉源在高考的當口意識到,“不能過早結束我的夢想。”2013年,他在微博上結識了一位知名棒球人,為自己爭取了去加拿大打球讀書的機會,一年后,他被美國球探相中,不僅拿到了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也得到了全額獎學金。
剛到美國時,劉源有些不習慣。畢竟,在加拿大讀高三時,他寄宿在一個冰球家庭里,時常和全家人一起去看冰球賽或是在院子里和弟弟妹妹們玩耍,始終充滿家庭的溫暖,“教練家里5個孩子,4個都打冰球,一到周末有比賽,全家都會去場邊助陣。”但在美國,劉源只能形單影只。
就讀于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所公立社區學院,劉源能參加的賽事級別為全國初級大學體育協會(NJCAA)的一級聯賽,要想實現夢想,“先被大聯盟的球隊選上是第一步,然后去大聯盟所屬的小聯盟球隊打拼。”但現實中,不少年過30的小聯盟球員還在為進入大聯盟而努力,劉源十分清楚現實的殘酷。
和劉源同在丹佛小鎮上的還有一個中國女生,由于經常代表學校參加排球比賽,“常上報紙,小鎮的人都認識。”但更多時候,教練希望兩個中國孩子能多和外國朋友相處,“盡快克服語言障礙,適應他們的思維方式。”在這過程中,劉源把棒球作為溝通的途徑,努力尋求認可,“我每天5點起床,訓練完還要去圖書館,如果成績沒有超過標準,我比賽的資格也就泡湯了。”
原想著出國后學業能得到“解脫”,沒想到曾經“耽誤”了學習的棒球,現在竟成了讓劉源伏案奮筆的原因。這讓媽媽孫志云感到吃驚,“那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他說要上圖書館了,我和他爸都嚇了一跳,從小到大都沒有過這事兒。”但在寄予希望的同時,又擔心劉源吃不消,“有時看他回復‘嗯’、‘啊’,字不多,就知道他很累或是不開心,我就不再多問了”。
為了趕上球隊進度,劉源一年中在家的時間最多兩個月。他一直努力想當最后一個走出力量房的人,可總是會有隊友和他一樣加練到很晚才離開,“他們對棒球的執著,那種為了夢想的付出打動了我,相信努力是不會說謊的”。
令應瑜光沒想到的是,她的身材確實受到很多外國學生的認可,“常有人跑來問我怎么健身,甚至有人隔了幾個月來夸我‘上賽季進了一個漂亮的球’。”
同樣是校隊成員,應瑜光卻不是“被選中”的,這個在國內就自己組建足球隊的浙江姑娘,能成為加拿大薩省大學女足校隊成員,完全是因為毛遂自
“職業球員”曾經是應瑜光醞釀過卻被父母掐斷的夢,為了吸引專業教練的注意,她選擇到北京上大學,并在學校創建了一支女足隊伍,“沒有指導老師、只參加過一次北京高校聯賽,成績不好便沒有然后了。”那時,她常去清華“蹭比賽”,到了加拿大后,找校隊蹭球踢的應瑜光卻意外被接納,“結果第一堂課就差點兒練吐了”。
一小時100個俯臥撐、拿著25磅重的杠鈴片弓步走,幾堂課下來,身形嬌小的應瑜光竟有了令自己擔憂卻讓別人羨慕的肌肉,“太壯了不好看啊”,亞洲人的審美包袱偶爾會讓她對訓練產生猶豫,教練卻總在這時給大家鼓勁說:“你們的男朋友會很為你們驕傲的”。
令應瑜光沒想到的是,她的身材確實受到很多外國學生的認可,“常有人跑來問我怎么健身,甚至有人隔了幾個月來夸我‘上賽季進了一個漂亮的球’。”漸漸地,主動搭話聊天的陌生人多了,邀請她打冰壺、滑雪或健身的朋友也多了,有時,教授也會參與其中,“快40歲的人,不戴護具,踢起球來還特別猛,還是坐鎮中后場的清道夫角色,完全不害怕”。
關于身材的影響力,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李韜之也頗有感觸,“國外很多學生從小就有運動習慣,身體普遍壯碩,談戀愛都占優勢。”加上學校對體育的推崇隨處可見,“尤其是打NCAA(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級聯賽的隊員,除了可能享受全額獎學金外,還能享受別人崇拜的目光,比如進酒吧大家都要排隊,運動員刷臉就能進去,因為他們常出現在電視上”。
這讓很多中國留學生也躍躍欲試,李韜之笑稱,自己不少同學都是來自工科很強的高校,不乏“一說編程眼睛就冒光的DOTA(網絡游戲名稱——記者注)男”,但幾個學期下來后,“進健身房的轉換率能達到50%”。
此外,運動除了幫助留學生建立生理上的信心外,也能排解心理上的壓力。剛到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期間,李韜之有過一段語言適應的階段,“比如小組討論,他們說得很快,你聽不懂就沒反應,大家就以為你很笨。可每天和他們打一兩個小時籃球,熟了以后,他們便了解你的癥結在于語言,甚至會主動幫你解決問題”。
他有了在喀山組建中國留學生足球隊的想法,只是,他沒料到中國學生數量不少,找人踢球卻很困難,“對體育不感興趣的占多數,偶爾有打籃球的,踢球的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不會有那種美國校園的體育明星。”剛剛從德國慕尼黑理工大學畢業的朱曉玉表示,和美國、加拿大不同,德國學生的體育生活更加個人化,但選擇性很寬泛,“冬天滑雪、夏天去湖里游泳,還包括潛水、劃船、擊劍這些國內學校不常設的課程。”但通常情況下,學校會提供場地和體育課,學生需要注冊,且按照不同課程來付費,“基礎卡大約8.5歐元一學期,如果到20幾歐元,便可以使用健身房”。
朱曉玉發現,僅憑對體育的愛好,想融入當地的社交圈并非易事,即便周末彼此會邀約去森林徒步、有球賽時亦會三五成群在酒吧看球,“但對看重個體自我成就的德國人而言,體育能增加對你的好感,不代表會輕易接納你進入他們的圈子。”因此不難理解,著名球員施魏因施泰格騎車買咖啡時會被外國游客索要簽名,但旁邊的市民卻無動于衷。
所以,喜歡打籃球的朱曉玉最終結識了一幫中國球友,從陌生到熟悉,時常也能在異國湊個飯局,而德國的球伴“通常打完球就散伙兒了”。
可對于在俄羅斯喀山留學的王時禹而言,“把中國留學生聚起來”是他想主動做的事。這個對足球癡迷到會在周末用衣服捆個圈,效仿貝克漢姆朝輪胎射門的東北男孩,曾經在俄羅斯參加過學校里以“國家”為單位的比賽,無奈中國學生難以成隊,他只能混在“雜牌軍”中“輸得特慘。”去年,他有了在喀山組建中國留學生足球隊的想法,只是,他沒料到中國學生數量不少,找人踢球卻很困難,“對體育不感興趣的占多數,偶爾有打籃球的,踢球的基本上沒有。”于是,籌備了約3個月,包括幾名零基礎的隊員,球隊才形成了8名主力兩名替補的陣容,每天晚上由王時禹指導訓練,“不怕現在實力差,慢慢就能練起來,好歹是原汁原味兒的中國隊,有歸屬感”。
作為俄羅斯的“體育首都”,喀山不乏體育氛圍。到主場比賽的周末,王時禹會帶著花幾十元買的球衣去現場支持喀山紅寶石足球隊,平日里各大高校及留學生組織舉辦的賽事也不乏參與者,甚至還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世界游泳錦標賽等國際大賽,只是與王時禹一同為體育奔走的,始終鮮有中國學生的面孔,“還是在宿舍里宅著的比較多”。
比賽時下起了瓢潑大雨,隊員按要求離場,被澆透的李韜之剛站起來,身旁的死忠球迷就問他:“你去哪兒?難道你以為這等于比賽結束了嗎?!”
觀看主隊賽事,算得上能讓中國留學生融入當地體育文化最迅捷的方式。李韜之還記得首次觀看密歇根大學狼獾橄欖球隊的主場比賽,沿途都有賣球衣的小棚子,“所有人穿的都是標志上的藍色和黃色,穿個其他顏色的衣服都沒法兒走”。
位于密歇根大學中的密歇根體育場,堪稱世界上最大的校園球場,至今維持了連續250余場上座率超過10萬人的紀錄,“也就是三四十年球場有比賽時都處于爆滿狀態。”李韜之放棄了賽季前收到學校推送的250美元季票,到現場才發現“單張已經賣到了300美元”,但他依然坐進了黑壓壓的觀眾席。“第一場對東密歇根,贏面很高。”但比賽時下起了瓢潑大雨,隊員按要求離場,被澆透的李韜之剛站起來,身旁的死忠球迷就問他:“你去哪兒?難道你以為這等于比賽結束了嗎?!”他待在原地往四周看了看,發現無論20歲還是60歲的球迷,都在電閃雷鳴中穩坐在原地,等比賽重新開始。
從那之后,他便真心實意地坐在那座球場里見證了菲爾普斯等校友回歸、老兵紀念日時為球場工作了四五十年的工人站在球場中央,“高質量賽事加情感的引導,很容易建立學生的榮譽感。”李韜之現在能隨口說出球場的設計容量為“109901人”。
這種橄欖球的精神,周圓在實習的日本公司里也體會過,“創始人曾經打過美式橄欖球,所以剛進社時,他們介紹的經營理念都能看到橄欖球規則、技巧的影子。”在日本筑波大學學習健康增進學的周圓表示,對體育的崇尚在很多日本企業中都可窺見,“通常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為20萬日元,但有籃球特長的學生如果被公司簽約打球,一開始便能有五六十萬日元的收入。同時,在求職投簡歷時,會留出專門的一欄填寫你的體育特長,有體育技能的人會受到青睞。”但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人們把體育和健康密切聯系,運動教室同樣會請專業講師講解老人、孩子等群體的牙齒保護、如何吞咽、三餐搭配等非常細致的問題,這啟發她決定在職業方向上關注老年人的健康問題,周圓在本子上謄抄翻譯了一套健身動作,“準備回國給家里老人試試”。
“專業課的討論,中國學生喜歡用奧運會作案例,其他學生則集中在職業體育。”李韜之同樣感受到課堂上中外留學生對體育認知的差異,甚至雙方選擇體育管理專業的目的都不太一致,“以前的同學,高考上來可能并不想選這個專業,學的時候也不知道將來如何使用。
但國外這個專業已經非常細化,需要帶著職業技能的訴求來上課,你要做賽事運營、還是場館管理等等,職業規劃方向非常清晰。”
基于這種差異,李韜之回國后選擇創業,成立了一家體育留學咨詢公司,依托市場需求,生意“比預期好”。但“很久沒能打籃球”依然讓他有些困頓,“即便有時間,想約一群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球并不容易,況且不是天冷就是霧霾,我只能找地兒跑跑步了”。

學習動物營養學的應瑜光(右二)與同學參加室內五人制足球賽。
當體育在國內處于教育評價體系的弱勢地位,在國外成為校園文化的強勢代表——體育何以成為中國留學生的敲門磚
在昨天抵達加拿大多倫多前,英達的行程多與冰球有關——作為領隊,帶領北京隊小選手參加國家少年隊選拔賽;作為嘉賓,出席加拿大大使館的冰球晚宴。現在的英達,除了“著名導演”的身份外,“冰爸”也成為他的標簽,正是兒子英如鏑的選擇,才讓他樂此不疲地跨海越洋。
英如鏑曾是名揚海外的“虎仔隊”成員,并在2007年,與宋安東、李歐等球隊中堅力量相繼赴美國、加拿大留學,成為中國第一批少年留洋冰球運動員。去年6月,宋安東被紐約島人隊選中,成為北美職業冰球聯盟(NHL)中國第一人,也被國內媒體視作“中國職業體育家庭模式培養的范例”。
據媒體報道,從宋安東10歲起,這個家庭開始長期兩地分居,父親每兩三個月往返一次國內與加拿大,母親則常年駕車帶著宋安東及弟弟奔波于各項訓練和賽事之間。而包括英達一家在內的中國“海外冰球家庭”,情況也十分類似。英達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早期的應試教育令部分留學生感受到體育競爭中的弱勢與不足,使得近年來留學生的年齡越來越小,“從我們那個時代出國讀研、讀本科,已經發展到今天的讀私立高中或初中,體育成績也在錄取中越來越重要。”而北美流行的冰球,恰是不錯的選擇,“不要求超常的身高體重,更適合頭腦聰明擅長技術的中國孩子,如果這孩子湊巧很勇敢的話”。
逾之更甚的,還有高爾夫、擊劍及馬術等個人項目。“因在美國,高爾夫普及程度遠遜于棒球、籃球、橄欖球,為此給準備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提供了入名校、申請獎學金的機會。”據美國《僑報》報道,高爾夫已被列入2016年的奧運項目,“目前許多準備送子來美留學的中國家庭,也在積極創造條件讓孩子投入高爾夫球的訓練,其目標并非奧運會”。
當體育成為叩開世界的“敲門磚”
2005年丁俊暉名聲大震后扎根英倫,2007年宋安東遠赴加拿大,都被著名體育學者易劍東視為“我國第六次留學熱潮”的一個變化,“自洋務運動、甲午海戰、上世紀30年代的軍事及科技人才留洋,到解放初期留蘇,至改革開放后的出國熱,尤其在后期,體育很少成為留學的目的。而丁俊暉和宋安東正是去國外尋求體育的發展,這代表了一個趨勢,包括現在希望去學習體育管理、運動康復等專業學科的學生,也包括發現體育項目可以加分,發揮其‘敲門磚’功能的孩子”。
“以美國的大學為例,有獨特體育特長的學生很受學校青睞,美國的體育社團非常多,每個體育社團都會要求美國的學校招生辦公室,留意相關體育特長生,鞏固自己的體育團隊,如果這個學校籃球社團缺少后衛,恰好這個學生的特長是籃球,那么他的錄取幾率就會大很多。”據金吉利留學美國六部咨詢師宋欣悅表示,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對于體育特長生青眼有加,且在項目上也有區分,“美國更喜歡棒球、橄欖球、籃球等,加拿大則傾向滑雪、冰球等,澳大利亞則看重潛水等”。
據記者了解,以德國為例的部分歐洲國家,對于有體育特長的學生鮮有優惠政策,且即便在美國和加拿大,如果并非體育專業能力特別突出、且因此被校方相中的留學生,體育技能通常只能增加被錄取時的“印象分”,幾乎沒有實際的優惠政策。但金吉列留學加拿大事業部顧問彭義雯表示,這種“印象分”不可忽視,因國外大學的評價體系非常注重人格健全,體育是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所以對選擇體育理論專業的學生而言,有體育背景的學生能更好地適應國外的授課模式,而普通學生則應在學習能力的基礎上,增加體育方面的知識,“男生可以盡可能多地了解球類運動,女生則可以學習瑜伽、舞蹈之類,甚至可以學習有中國元素的體育項目,這樣,出國后就能更快地融入社交圈”。
為何美國大學如此重視體育
之所以體育能充當留學海外的“敲門磚”,在易劍東看來,是因為體育是國外大學文化中最顯性的因素,尤其以美國最為突出,“除了在人際交往上更便利,對于人格完善的價值不可替代外,不排除高校也有開拓中國體育市場的愿望”。
“目前包括哈佛、耶魯等名校在內,拿到通知書不去的學生也有百分之十幾的比例,而體育就是招人的重要方式。” 易劍東介紹,美國的各個大學都有項目各異的運動隊,且校隊人數在學生中比例較高,“因此,體育和大家都能產生聯系。”而美國高校體育的市場化運作也十分成熟,體育已經成為各學校品牌彰顯的最顯性、最重要的因素,“中國家長朗朗上口的‘常青藤盟校’正是體育賽事的聯盟。每逢招生季,高校宣傳冊上的主要內容都是體育,其實更像招商宣傳冊。”對于美國高校而言,聯賽的成績不單是學校的面子,還是“搖錢樹”,因為大學聯賽的門票及電視轉播收入,比職業聯賽也差不了多少,“學校里薪水最高的人往往是教練”。
去年底,美國西海岸的體育高校聯盟 Pac-12主席斯科特帶領兩支籃球隊到中國交流,他向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這個由12所美國高校組成的聯盟擁有7000多名運動員,如果把聯盟中的運動員組成一個國家,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拿到的獎牌可以登上獎牌榜第五名,而且聯盟有自己的廣播電視網絡,可以播送850項體育賽事。“美國的大學體育文化是現象級的。”在密歇根大學畢業生李韜之看來,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高校無法企及的,“在國內,每年大學球隊的預算都不足以支撐宣傳,如果學校不給市場的宣傳資源,學生都不知道什么時候有比賽、去哪兒看。但在美國高校里,時刻都有體育,競技的奇跡和懸念,很容易讓人產生自豪感。”斯科特認為,這足以帶動“校友的力量”,“目前,有2.1萬中國學生在聯盟的學校,他們會不自覺地成為大學體育的粉絲,這些校友就是聯盟發展的驅動力”。
冬奧冠軍楊揚在國內經營冰上項目的培訓,她曾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越來越多有留學經歷的孩子會在假期上冰“補課”,期待能更好地融入國外學校的體育氛圍。但她也強調,隨著更多孩子對體育的熱愛,家長急功近利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不僅是把奧數換成體育項目,更明白體育對孩子全面發展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被培養起體育興趣的學生,一旦處于“體育不易被認可的國內教育評價體系”與“既有利于延續體育愛好又能借此得到升學機會的留學之路”間,選擇并不太難。
在易劍東看來,在體育上幾乎相反的教育評價體系,是導致中美高校體育文化出現巨大差異的關鍵,讓更多人走出國門體驗真正的體育利大于弊,“國內的體育理論很貧乏,技術上真正過關的也不多,當這些人回來后,不僅能帶來更先進的理念,也可以踐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影響他人,后發的體育國家或能進步千里。” 首都體育學院校長鐘秉樞同樣表示,“以前蔡元培提出,完全人格首在體育,但這種認識在今天的校長中不多見了,如果要真正做到國內和國際接軌,就需要轉變觀念。或許,北大清華今年對足球特長生敞開大門,就是一種轉變”。

在中國學習武術的菲力希望成為中國武術文化的傳播者。 菲力/供圖
武術是首選,踢球能交友——
外國留學生也有本中國體育經
當捷克小伙兒馬原回到首都體育學院繼續學習漢語和武術時,來自德國的“師兄”菲力還在世界各地拍電影、進行武術演出。
2013年,菲力為馬原制作了一部15分鐘的紀錄片,記錄了他在首都體育學院作交換生最后一周的心情。方塊字和刀槍棍棒占據了馬原的整個白天,僅有的生活片段,是中午馬原穿著短褲趿著拖鞋,從訓練樓出來到食堂去吃碗面。
到了周末,馬原會去教小學生習武,但指導鬧騰的孩子,對中文還不夠流暢的他來說,既是機會,更是挑戰。當馬原認真地示范踢腿的時候,兩個扎著辮子的小女孩在身后揪他的衣角,他一愣,又好氣又好笑,“或許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覺得他們好像不太尊重我。”而幾個孩子則嘰嘰喳喳地告訴菲力,他的語言能力還要提高。
有時,馬原和菲力會和武術隊的中國學生一起練習,馬原站在旁邊看,心里十分糾結,“我很郁悶,他們的水平那么高,我根本就趕不上,但每天看這些招式,又會覺得充滿動力。”在中國的一年里,穿著一雙用毛筆寫了“武”字的白色武術鞋,馬原在墊子上翻轉騰挪度過了大部分時光,對他而言,這算得上是最幸福的事,“武術有很多種類,自衛防身、套路、拳術和器械,選擇很多,但保護和指導也得跟上。在歐洲,我只能自己在戶外練,沒有老師,常常受傷,進步特別慢。因此,這里的訓練條件和中國生活方式,讓我舍不得離開”。
一年后,馬原再次回到首都體育學院繼續學習,但為他拍攝視頻的菲力已經畢業了。自2010年來到北京后,菲力便一心想成為留學生中研習武術的佼佼者,在高手云集的全國大學生武術錦標賽上兩次拿到第三名,也讓長相帥氣的他在熱衷武術的留學生中小有名氣。
10多年前,一個“來自少林寺的中國人”在德國比勒菲爾德開了武館,想模仿功夫電影動作的菲力兄弟倆馬上拜師學藝,“在德國還有別的功夫學校,但老師不是中國人,教的武術不地道”,所以,“即便中國老師不會德語,但我們一點兒都不介意。”少林功夫豐富的動作和高難度,讓菲力“一開始學就愛上了”,從此,到中國學武術就成了他23歲時最想做的事。
盡管已經畢業了,但菲力“遲早要回來”,因為他所學的專業民族傳統體育,在國外很難被廣泛認可,他傳播武術文化的方式并不豐富——在各種背景和燈光下,和同伴用拳腳展現著中國武術的神秘,可除了“神秘”,武術的概念很難在沒有中國文化生根的地方為人所熟悉,“我想過教德國人武術,但他們學起來非常困難,所以,我想以此專業回德國找工作,幾乎不可能”。
但對外國留學生而言,要想找到適合自己的群體,武術這樣的中國傳統體育項目未必是首選。2008年來到北京時,是足球幫助喀麥隆小伙兒詹姆斯迅速成為一個“中國通”,并借此找到歸屬感——因為滿嘴東北味兒濃重的“哎呀媽呀”,詹姆斯被“夢之隊”看中當了翻譯,而能加入這支由常駐北京的非洲外交人員組成的球隊,除了他本人是華北電力大學的公派留學生外,與他在大使館工作的哥哥也有關系。詹姆斯很喜歡這個團隊,“和他們踢球,不會太計較輸贏,就圖個開心,像家人一樣”。
但成為“中國通”,正是詹姆斯和中國人踢球的收獲。北京著名的民間聯賽回龍觀超級足球聯賽,成就了詹姆斯一口流利的中文,也讓他結識了一群五湖四海的朋友,“可惜就是沒人給介紹個女朋友”。初來乍到的詹姆斯,一開始連“大家辛苦了”這句話,都難以在漢語和法語間切換,但幾場球踢下來,他的中文水平迅速提高,甚至在趙本山的小品和《鄉村愛情故事》以及北京國安現場氛圍的影響下,他還練了一口頗具特色的東北話和北京話,他下巴一揚,故意作出很顯擺的樣子,“我愛國安,因為球迷很瑟。”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