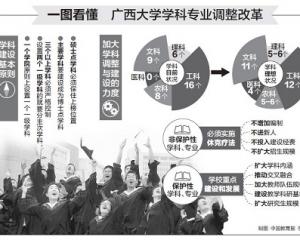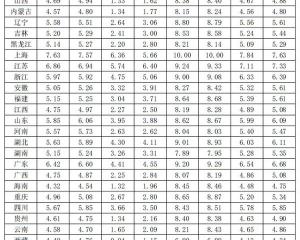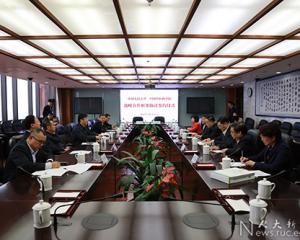再吼一次青春的歌(圖)
導讀
那是口水軍團樂隊誕生的時代:沒有霧霾,城市不大,路沒那么堵,也沒那么忙。
對于大部分人循規蹈矩的那一代,就是因為音樂中蘊含的叛逆和不羈,反而激起了更多共鳴......
耀眼的燈光從18米高的頂棚上打下來,舞臺上的董磊似乎一下子就找到青春的感覺。他甚至忘記了自己是兩個孩子的父親、生意場上忍氣吞聲的乙方。只剩下熟悉的旋律驅動微胖的身體在舞臺上蹦蹦跳跳,跟曾經最好的兄弟在一起。
手機在拍,相機在錄,2400平方米的影棚里擠滿了男男女女。歌迷攀上觀眾區的欄桿,跟著臺上一起怒吼,還有人伸長胳膊比劃著我愛你的手勢。
狂熱,躁動,有時還夾雜著一種不知道從哪里來的憤怒。
已過而立之年的他,記憶中的青春期應該就是這個樣子。那時,他染著顏色怪異的頭發,玩各種各樣的搖滾和說唱樂。
1999年,這個當時只有17歲的杭州男孩,和吳瓊、汪洋、馮飛、明明等幾個朋友一起組建了一個叫做口水軍團的樂隊,用杭州話玩說唱,宣揚杭州話罵人精髓。在董磊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里,幾個人很快攢出來一首歌,叫做《人兒登》,并傳到網上。
誰也沒想到,歌就這樣紅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幾乎大家都在討論這首歌是誰唱的。他們也開始走到聚光燈下。他們的故事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甚至在一部名為《長大的故事》的紀錄片中,這群出生于80年代初期的杭州小伙子,被當成中國首批獨生子女的一種典型。
可是后來,樂隊玩著玩著就散了,連個散伙飯都沒有吃。曾經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泡妞都在一起的兄弟,聯系也越來越少了,就連這些80后的青春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今年5月,樂隊解散12年之后,董磊才第一次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以口水軍團的名義,辦一場演唱會。為此,他們還發起一個眾籌項目,名叫杭罵唱到爆的壞孩子們,來場告別演唱會。
人到了這個歲數,也想做點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兒。對于我們來說,就是想辦場演唱會給年輕的時光畫一個完美的句號。董磊哈哈大笑,一串金剛菩提佛珠在白色的襯衫上蕩來蕩去。
遇到一種中年的危機感,慢慢不被社會重視了,就會想做一些事情彌補這些失落感

就在5月的那次聚會后,口水軍團的眾籌項目上線了。除了一篇介紹文章,還有一個口水軍團原成員一起拍的短片。
片子里幾個中年人一起喝酒,聊天,抽煙,壓馬路,就像又回到了年輕的時候。
口水軍團對你代表著什么?在那部7分鐘的片子里,汪洋問。
當時那段時間,就是代表了我的整個青春期吧。馮飛說。
對于這些步入中年的人來說,回憶青春并不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程。2014年口水軍團成立15周年的時候,董磊就曾有過辦演唱會的想法,最終因為找不到贊助資金,又擔心自己出錢,沒有足夠多的觀眾,收不回成本。
眾籌的想法最后付諸實施,起源于董磊最近在一家叫做開始眾籌的網站策劃一個叫做創造力的項目。策劃項目時團隊撓頭苦想怎么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故事,這時一位25歲的姑娘突然說:口水軍團來次眾籌就不錯啊。
董磊這才下定決心。我覺得眾籌是一種生活方式,就是我一直在做一件非常喜歡的事情,也有一些成績,你們可不可以幫我完成一些夢想。他說,而且我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還有多少影響力,有多少同時代人還記得這段記憶。
沒有人想到,眾籌的項目很快就達到了目標。
5月17日晚上10點上線的眾籌,不到24小時籌到了7萬多元。發表在微信公眾號上的推薦文章,幾個小時之內的閱讀量就超過10萬。到眾籌截止日,2015年6月17日,口水軍團籌到204133元,超過了他們的目標金額。
口水軍團自己拉了一個微信群,5個人在里面特興奮,所有人到凌晨3點,還在發信息。
那天晚上微信朋友圈基本上被刷屏了。回憶起眾籌開始時的熱鬧,董磊依然很興奮。
這有點像他們的青春歲月。那時,口水軍團的成員充滿了激情。
董磊不到10平方米的臥室里,擺著一臺舊的奔三電腦,里面裝著他剛剛學會使用的水果音樂制作軟件。這臺老電腦和一個8塊錢買的電腦話筒,就是他們音樂創作的全部設備。
大多數時候,董磊趴在桌子上做著音樂,身后幾個人坐在床上聊天,講笑話,哈哈大笑。等到曲子做完了,再由大家一起填詞,每到這個時候,吳瓊和汪洋就會說我肚子疼先去上廁所。董磊笑著回憶道。
在一起,他們玩了幾年。在那篇介紹文章中,董磊回憶道:那是口水軍團誕生的時代,沒有霧霾,城市不大,路沒那么堵,也沒那么忙。城里的很多同齡人跟我們一樣,混著,玩著,好著,壞著,開心著,傷心著,戀愛著,孤單著
而如今一切都變了。樂隊解散了,從四面八方聚起來的兄弟們,又奔向了四面八方。這么多年間,他們甚至很少聯系。
董磊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公司,曾為捍衛自己音樂見解不惜和兄弟吵架的他,什么活兒都接。音效制作,各類影視、動畫節目配音,活動策劃。
現在有些甲方很賤,以前都把你當狗一樣使喚,說董磊啊,這個事情你去搞搞掉,一旦知道我曾經是口水軍團的,就立馬把稱呼改成董老師。董磊惟妙惟肖地模仿著。
有時候,他覺得做商業音樂就好像老是在被人家強奸,需要考慮的不是好的音樂創作,而是琢磨客戶說的每句話。廣告公司一句這個不是我要的,董磊就得琢磨到底哪個東西不是對方要的。你要研究的不是你的技術,而是他媽的心理學,神經病嘛這,你到底在做音樂還是在他媽猜人啊。
他甚至不愿意向別人提起那段年輕的時光,每次說起來,人家都會說,哎,你給我們唱一段。他覺得這真的很煩。
頗豐厚的收入讓董磊把年輕時夢寐以求的音樂器材都搜集齊了,卻在實際工作中離音樂越來越遠。人們很難把這個發福的,對誰都笑呵呵的中年人,和曾經用最底層的杭州話說唱的年輕人聯系在一起。
不過在心底深處,他還是希望那段光輝歲月被人們記得。
那個時候關于生活真的沒有想太多,年輕人也不太會去考慮怎么規劃,怎么經營自己的人生,每天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

中年的危機感不止在董磊的生活中彌漫。
口水軍團成員明明做過生意,賣過兩年服裝,因為受電子商務的沖擊,也做不下去了。2009年,他去上海待了四五個月,做DJ。但是又感覺上海對外地人有歧視,終于又回到了杭州。
軍團成員馮飛端起了照相機,從零學起做了一個攝影師,幾乎完全跳出音樂圈。
另一成員汪洋也忙著謀生。他在樂隊解散后先是帶著幾個人做自己的廣告公司,后來團隊一并加入了太太的家族企業。
當時真是窮的沒辦法了,不得不去干活兒。汪洋說。見到記者時,他剛結束一個會議。時間是下午1點,還沒來得及吃午飯。
有時候,想想真的是不知道青春什么時候就結束了。汪洋嘆了一口氣說。年輕時候混過十幾個圈子的汪洋,如今每天為工作上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他早已把曾經的愛好收拾起來,開口閉口談的是企業管理。
汪洋曾經有種想法,把年輕時玩過的事物,每項留下一兩件紀念品,陳列在辦公室里。但是這些散落在各處的物品,實在太難打撈了。
而那段青春歲月完全不同。那幾年,杭州房價剛開始上漲,不過這些剛剛走出學校的年輕人并不擔心這些。董磊把自己賺到的幾乎每一分錢都用來買樂器,而馮飛則因為樂隊排練,一聲不吭就辭了職。
每天都是蹭吃,蹭喝,蹭睡。坐在錢塘江邊的咖啡店里,馮飛說。曾經有幾天,他天天混在汪洋家,把他家的米都吃完了。汪洋也有一段時間天天住在董磊家,以至于董磊的母親對他都沒什么好臉色。
汪洋記得,那個時候幾個人窮極了。到飯館里只敢點最便宜的拌面。三塊錢一碗的面,還要懇求老板能不能來半份。
《賤兒飯》(意思是吃飯不給錢)就在這種狀態下被創造出來。賤兒飯,老酒吃飽;賤兒飯,表(不要)付鈔票;賤兒飯,賊頭狗腦;賤兒飯,苦頭吃飽。
那個時候關于生活真的沒有想太多,年輕人也不太會考慮怎么規劃,怎么去經營自己的人生,每天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那就寫首歌玩玩。董磊說,每首歌寫完都很激動,我也能寫出這么好的歌。
《賤兒飯》寫出來,口水軍團真的火了。一位當時上初中的女生記得,這首歌成了他們的班歌,時不時都會拿出來唱。對于不少杭州的80后來講,這首歌和周杰倫的專輯,一起成為他們叛逆時期的音樂記憶。
外表文靜的小吳,到現在仍然記得在那個MP3還不算流行的年代,她把錄有口水軍團音樂的MP3藏進寬大的校服里,躲著老師偷偷聽的歲月。在杭州一所重點中學讀書的小祁,則會在每次到KTV的時候,拿著話筒吼兩句《賤兒飯》過癮。
我們這一代人大部分都還是循規蹈矩的,雖然心里面會偷偷地想著怎么肆意妄為一下。所以聽到他們歌詞里那些不入流的話,就有一種莫名很爽的感覺。回憶起這些用最底層杭州話寫成的歌曲,一位已經在北京讀研究生的杭州80后說。
那段時間,就代表了我的整個青春期吧

已經跳出音樂圈子的馮飛和汪洋,幾乎很少有機會仔細審視到那段記憶。工作之外,汪洋更愿意陪伴女兒和妻子。
年輕的時候就是把自我放的很大,一切都要滿足自己的需求,現在則盡量把自我壓縮,更多考慮家人和朋友。汪洋感慨,年輕的時候該玩的都玩過了,現在到了還債的時候。
對于其他人來說,那段記憶甚至變得有點不合時宜了。外號叫蒼蠅的沈磊嘉一天晚上去泡吧,別人介紹他:這是當時口水軍團的,是夜店妹頭(很多女生追求的人)。他看了看自己漸漸隆起的腹部,一臉大叔相,變得有些感傷。
但是無論如何,那些記憶隨時都可能被觸碰到。
董磊記得小時候杭州的巷子里,到處都是香港四大天王的歌曲,可是他一點都不喜歡。初中開始組樂隊的時候,玩的就是搖滾、朋克。馮飛和汪洋也是如此,在琴行里排練時認識的這兩個人,一見面就聊激流金屬、死亡金屬、粘合
無論是搖滾還是說唱,在我看來都有類似的效果。多年以后,馮飛想起那段歲月時說,那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自己想的東西表達出來。
1997年,董磊16歲,因為老師把沒有寫完的作業摔在了他臉上,他就用最臟的杭州話和老師對罵起來,并從此輟學。
輟學以后的董磊在餐廳端過盤子,也到酒吧做過DJ,沒有一項能夠長久堅持下去。只有樂隊,做了一個又一個。在這個過程中,他先認識了吳瓊,然后又認識了馮飛和汪洋。
玩音樂是這些人湊在一起的借口。聚在一起,從網絡游戲到科幻電影,甚至黑客攻擊,沒有一個不是他們發泄青春的方式。
當時基本上處于瘋玩的狀態。汪洋回憶。做過一段黑客的他,曾經黑進過杭州所有重要的網站。后來,在吳瓊的攛掇下,他又喜歡上了摩托賽車。結果兩個窮小子,一個人買了一輛雅馬哈,另一個人買了一輛本田的公路賽車。
90年代末的杭州,并沒有很多可供這些年輕人玩樂的場所。每當夜幕降臨,市中心的銀泰廣場門前,裝下了幾乎所有這些被街頭文化吸引的年輕人,和他們的青春躁動。他們在這里比拼炫技,見網友。
蒼蠅幾乎每天放學都來到這里,父母沒法阻止他,就切斷他的經濟來源,可是他卻學會了到當地的批發市場淘衣服,200塊錢能買一身衣服。后來父親威脅不給飯吃,他就自己在家用剩米飯做蛋炒飯,最終作為青春的留念,他學會了用各種各樣的材料做蛋炒飯。
2003年3月22日晚上,吳瓊和汪洋帶著各自的女朋友一起打了一整個通宵的游戲,第二天一早,吳瓊要騎摩托車去兜風,汪洋覺得太困就沒去。
然后再次聽到吳瓊消息已經是3月24日了。這天杭州《都市快報》上刊登了一則消息,稱23日中午,04省道余杭區百丈鎮泗溪村公路出口處,一群杭州青年高速駕駛摩托賽車飆車至此,其中一名青年在拐彎時不幸撞向公路旁的護欄,飛跌溝渠,當場死亡,摩托車出于慣性還往前飛出200多米。吳瓊騎的,就是他年輕時唯一擁有的那一輛本田賽車。
吳瓊是口水軍團里最會玩的人,最后也真是玩死的。董磊說。幾個整天嘻嘻哈哈的大男生哭得稀里嘩啦。
為了紀念吳瓊,明明、馮飛、汪洋,把董磊和蒼蠅找回來,一起做了口水軍團的最后一首歌《Made in 杭州》。里面有句歌詞:雖然我還不是毛(很)懂撒(什么)個HIP-HOP MUSIC,但是我會好覺聽他們到底表達撒西。
汪洋把吳瓊的死當作口水軍團的一件里程碑事件。他絕對是個二貨。汪洋手托著腮,眼睛盯著墻面說,但是他沒了,我們的快樂就沒了。
再后來,口水真的就慢慢散了,從一群男人的生活,回歸到正常人類生活(談戀愛、結婚)。
聽說你們要辦演唱會,一定要讓我跟著玩一下

快要被繁瑣生活淹沒的5個人,決定讓口水軍團和那段青春的記憶一起重見天日。
蒼蠅主動請纓。這位為甲方搞過各種活動演出的創業者,也愿意為自己搞一次演出。
他是最后一個加入口水軍團的。在此之前,這位就讀于職業高中的孩子在街頭玩滑板、玩涂鴉,還組織過杭州第一個滑板隊。他至今記得踏著滑板掃街時行人停留在他們身上的目光。
如今,沈磊嘉的公關公司隱藏在杭州市中心一個外觀看起來有些破敗的三層樓房中,雜亂的辦公室里只有幾雙顏色艷麗的潮牌鞋能讓他想起以前的歲月。
雖然有時候仍然會買票去看看現在年輕人玩說唱和滑板是怎么樣的,但是閑暇的時光,他更愿意載著家人去附近的千島湖景區,躺在草地上待一下午。
以前玩滑板也好,做音樂也好,人家出去看見你都一副崇拜的表情。蒼蠅把身體攤在黑色的皮質辦公轉椅中說,但是現在還是蠻容易被打擊的。
剛剛開始創業的那段時間,蒼蠅的大量資金被投進公司里,甲方的錢到年底收不回來是常有的事,頭一兩年每到年底,他算賬以后都難免感慨又給員工打了一年工。年少時曾經無所事事,到處游蕩的蒼蠅,如今特別害怕閑下來,害怕自己沒有業務的時候,看到朋友圈里其他競爭對手正把活動搞得火熱。
因此一聽到董磊的提議,蒼蠅就兩眼放光。
可真做起來,難度不小。各自奔波這么多年,都有自己的家庭一攤事兒,即使大家聚一聚,都顯得奢侈。
這不像他們年輕時候。當年,他們有的是激情,說干就干。就像明明加入時一樣。
加入口水軍團之前,20歲的明明還是浙大音樂系鋼琴班大一的學生。在網上聽到《人兒登》(意思是一個自我感覺很好,做事卻糊里糊涂的人)以后,眼睛都直了。
與另外幾個人素不相識的他,直接在網上留言,我要加入你們。樂隊就這樣多了一個成員。
口水軍團多年以后的第一次聚會,被安排在杭州濱江新區的一家星巴克。從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趕過來的幾位樂隊成員用普通話聊著天兒,感覺挺商務的。
直到快10年沒和其他人見面的明明說了一句,我們大家不要這么正兒八經的,好不好,都是兄弟、哥們兒,大家才從星巴克挪到了燒烤攤,一直聊到凌晨兩點。
董磊本來的打算是,把這次演唱會辦成一個只有兩三百人參加的小型派對。可是線上線下的熱情超乎他的想象。一位專門為各種演出提供音響解決方案的朋友得知消息后,主動給他打電話:聽說你們要辦演唱會,一定要讓我跟著玩一下。最后,小型的派對變成1000人左右的規模,場地和音響燈光設備全部靠朋友幫忙。
為了這次演唱會,董磊在籌備的幾個月時間里推掉了所有的工作,蒼蠅則提前就跟老婆打招呼,這段時間就不要查崗了。
但即使這樣,幾個人還是越來越難聚在一起。以前最不在乎時間的他們,開始很難協調排練時間,公司事務繁忙的汪洋甚至一度提出退出。后來,是董磊告訴他,要讓孩子知道爸爸曾經很牛逼,他才努力堅持下來。
除此之外,他們還計劃在每首歌的后面,用投影儀把吳瓊小時候的照片投放在身后的環繞大屏幕上,就好像他也在現場。
但遺憾的是,臨開場的時候,投影儀壞了,吳瓊的照片最終沒能出現。
把這段記憶封存起來,不再破壞它
演唱會在8月22日開始。在這個演唱會上,口水軍團演唱了10多年前的成名曲。
1986年出生的小祁早早就來到現場,把著最靠舞臺的位置,還有歌迷從上海趕過來,身上還穿著工作時的襯衫西褲。這是一個熱衷本土文化的人,得知這個消息后,他決定要品味一下宣揚杭州話罵人精髓的歌曲。他在第一時間就購買688元的眾籌套餐,里面包含一張演唱會門票。這還是他第一次購買演唱會門票。

就連董磊的老婆,也偷偷買了這一檔套餐。
演出前幾個小時,在后臺準備的明明和汪洋緊張得說不出話,距離演出一個半小時的時候,汪洋還偷偷溜出后臺,到檢票口看看來了多少人,人家不來怎么辦?會不會有人買了票也不來?我們在臺上會不會怯場?會不會表現得很做作?
而10多年前則不一樣。他們隨時可以操起樂器,玩上一陣。2002年,杭州舉辦了西湖啤酒節,樂隊演出了整整兩天,在他們之前幾天出場的包括唐朝樂隊、汪峰和鮑家街43號、阿凡提樂隊。各種各樣的采訪排上了日程,本地的、外地的。甚至還有中央電視臺。
那時,他們從來沒有感覺到緊張。
不過當站在臺上,燈光開啟時,汪洋感覺以前的歲月一下子又回來了,就是那種渾身被腎上腺素充滿的感覺,好久沒有這么開心了。
演唱會晚上10點結束,幾個人又被大家圍著拍照、采訪,這群整日為工作奔波的中年人,一下子感覺像明星一樣。
現在回想起來,董磊對這種結果很滿意。其實通過這次演唱會復一下盤。他說,你在杭州總要借用一些渠道什么的,成為一個小名人之后總會更方便一點。
不過汪洋說,對于他來說,那天讓他回味最多的感受,還不是被工作人員像明星一樣包圍,而是演出結束,女兒飛跑著撲向他的懷抱。
等到所有人散場,藍色的卡車倒進現場,臨時搭起來的鐵架子又被收了起來。這些曾經的兄弟則跑去喝酒喝到不省人事,就像年輕時的某一個平常的夜晚。
那天晚上,董磊在朋友圈更新了一條信息。明明在下面跟帖:我真的愛你們。汪洋又回復明明:我們也都愛你的。
其實在籌備演唱會的時候,他們想過口水軍團重新走在一起的可能性,但是對于這一群已經各奔東西的人來說,看起來已經不太可能了。
現在做,做到那么好也不太可能,如果做不好也沒什么意思,這樣還不如把這段記憶封存起來,不再破壞它。董磊說,最重要的,是演唱會讓大家跟著我們high一次。
第二天醒來,所有人都還要繼續之前的工作。蒼蠅拿出手機刷了刷朋友圈,發現不再有人為他們刷屏,他忍不住到曾經的微信群里喊你們在么?我好想你們!也沒有人回應。他才意識到,自己又變成一個普通人。
最后,蒼蠅在家待了一天,整個下午都坐在陽臺上看著杭州市路面上繁忙的車來車往,一句話也不想說。
總感覺這么絢爛的東西,怎么就啪的綻放了一下,突然就沒了。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