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演講遭潑糞 性教育缺失并未因學歷提升而改變(圖)
會場內教師們探討如何開展性教育 會場外抗議者在喊反對口號
大學推廣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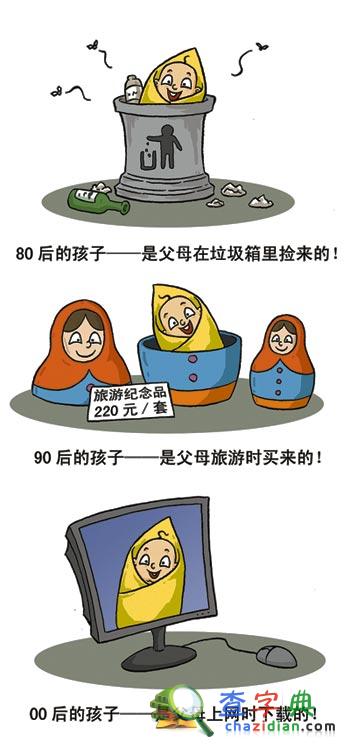
就像生活在兩個輿論場里。
一個是屬于性教育的“天堂”,這里有頗受學生歡迎的課程——把一個個在高校擔綱性教育的教師塑造成“學術明星”,以及深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另一個是性教育的“地獄”,任何有關性教育的風吹草動,都能招來一批反性教育的斗士。在這里,性教育從業者成了眾矢之的,而每一次反性教育的活動,也都能將性教育與“爭議”兩字裹在一起,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性教育學者、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就在這兩個輿論場之間不斷游走。只是,在他看來,“天堂”并不常見,“近些年有些高校開了性教育的課程,有的也確實火爆,但從數量上來看并不多,甚至可以說遠遠不夠,也就10所左右”。
至于“地獄”,前不久他剛“走”了一遭。
性教育老師演講遭潑糞
事發地在濟南,和在大學一樣,方剛扮演的同樣是老師角色,只不過,這一次他所面對的是幾百名專職教師。
根據方剛的回憶,參與培訓各方的積極性頗為高漲,整個培訓下來,他和與會的老師們探討了包括“在什么年齡對孩子進行性教育”、“采用什么方式進行有效的性教育”等不少問題,至于一些敏感問題,他們也沒有回避,比如,“家長和孩子一起看電視時,鏡頭里出現激情戲時怎么辦”,等等。
但與此同時,在會場外,集聚了不少“抗議者”,他們喊出“方剛滾出山東”的口號,稱方剛所講內容“是一種劇毒”。
方剛的培訓停了。
余下的行程安排也都被取消。這件事再次讓方剛意識到,象牙塔之外的社會,對性教育并不“友好”。
無獨有偶,就在幾個月前,在2014年年末廣州舉辦的一場文化節上,受邀出席的華中師范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彭曉輝,在演講時遭遇了一起更為嚴重的“抗議”——一名女性突然沖上演講臺,舉起事先備好的糞便,向彭曉輝當頭潑去。
而高校里有關“大學生為什么不能看A片”、“大學生為什么不能有婚前性行為”、“同性戀者婚姻為何不能合法化”等“彭曉輝語錄”也廣為流傳著。
科技的發展,對于知識的啟蒙理應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但在性教育這樣一個敏感領域,似乎幫了“倒忙”——反性教育的手段“升級”了。
對于濟南反方剛的家長群體,QQ群成了他們“聚眾示威”的最佳聯絡手段,一旦發現有人來做性教育的宣講,便在手機上聯合起來反對。
按照方剛的說法,“做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在移動互聯時代,他們常和性教育組織方說,“活動千萬別上微博,也別跟他人說,咱們偷偷地(做)就行啦。”
“濟南事件”發生后,那些曾經邀約方剛做講座的機構,“也不敢再聯系了”,方剛感慨,“我們的社會究竟怎么了?”
大學生性教育缺失并未因學歷提升而有改變
主流的性教育渠道難以打通,取而代之的就是低成本、零門檻的網絡渠道。但這些渠道里信息的真實和科學程度,則不被看好。
“學生們通過網絡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武漢大學“性與健康”課教師朱俊勇面對學生千奇百怪的問題,意識到大學生性教育的缺失,并沒有因為他們學歷的提升而有實質性的改變——
就在記者采訪的當天上午,朱俊勇還接了一個女學生的電話,稱自己懷孕了,但不知道該怎么辦。
這在成人聽來有些啼笑皆非,但對尚處在懵懂狀態的大學生來說,就是“天大的問題”。“我在課堂上已經給學生們講了很多避孕的知識,但依然會出現這種情況,何況那些沒有這方面知識儲備的人呢?”
一旦出現問題,就要學著向社會求助,這也是朱俊勇教給學生的。通過電話記錄來看,在當天的凌晨兩點多鐘,這位女學生就給朱俊勇打過電話,“這說明她心里非常焦急,懷孕了感到很無助,就像天要塌下來似的。”朱老師說。
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的一份數據也佐證了這一點,自2007年始,大學生因為比較普遍的婚前性行為及較少采取安全防護措施,成為新增的艾滋病高危、易感和高發人群之一。我國每年新染艾滋病的人中,約一半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當然,這更多地要歸咎于中小學階段性教育的缺失,在朱俊勇看來,高校的性教育,是對孩子在青春期本應獲得性教育的一種補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可能是最后的補課機會。
方剛認同這一說法。他說,“性教育傳授的不只是單純的性知識,還包括人的成長、價值觀的提升等‘如何認識某一件事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些是從網絡貼吧、論壇上學不來的。”
更為重要的是,有了這樣的課程,可以打通一個學生和真理之間溝通的橋梁,學生們會根據老師教的一些基本常識,去尋根究底,找尋應該怎么樣去做,以及為什么這樣去做。
“如果沒有這堂課,沒有向我咨詢這個渠道,她很可能找貼在電線桿上的小廣告,但那些大多是忽悠人的。”朱俊勇告訴記者,下一步,他準備在校內開一個咨詢門診,“就像心理咨詢那樣,做一個性教育的咨詢。”
提防偽性教育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藥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健提出將性教育寫入大學生教學大綱,一時引發熱議。
方剛稱,“類似的提議已經提了很多年,甚至相關政策也已經出爐了多次,為何仍開展不下去呢,還是社會觀念太過陳舊。”
此言不虛。北京師范大學腦與認知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文利曾做過一項我國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的統計,她發現,2000年以后,我國頒布過多個有關性教育的政策,比如2000年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就提到,“把原有思想品德課、思想政治教育課及青春期教育等相關教學內容有機結合進行, 幫助學生掌握一般的生理和心理保健知識和方法,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
2001年12月,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該法指出: “學校應當在學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適當方式,有計劃地開展生理衛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劉文利認為,這從法律上保證了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權利和學校應該承擔的教育義務,在中國青少年性教育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深遠影響。
2006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還頒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6~2010 年)》,其中寫道:對艾滋病防治和無償獻血知識知曉率,到2007年底實現校內青少年達到85%以上,校外青少年達到65%以上;到2010年底實現校內青少年達到95%以上,校外青少年達到75%以上。
遺憾的是,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實。
更為嚴重的是,方剛發現,不少偽性教育課程在高校“趁虛而入”。
多年前,一門名為“守貞課”的課程在浙江大學開講,因為其“一旦懷孕就應生育,流產是殘殺生命”、“婚姻外的性活動、特別是在青春期的性交從社會、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是有害的”等觀點,被媒體報道后引發爭論。
方剛就專門旁聽了一堂課,并當場提出批評,“這是一種典型的禁欲型性教育,說如果你不守貞,就會得艾滋病,就會被老公拋棄,這跟我們國家倡導的男女平等的國策是相違背的,我們不是反對守貞,但反對這種守貞教育,這是一種偽性教育。”
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大學生對于性教育的需求和推崇,“別說是學分了,就是有個性教育講座,大學生們就歡迎得不得了”,方剛說,但這門課如何開,是選修還是必修,誰來講,用什么教材來講,等等,尚需要學界乃至社會進一步凝聚共識后,才能回答。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