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巨齡:語言要花一生去琢磨-中國教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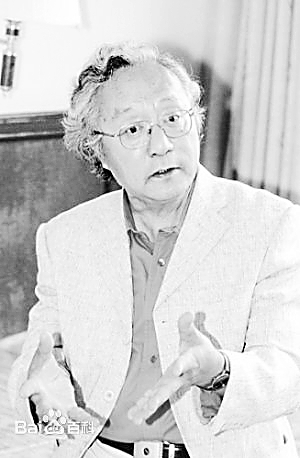
張巨齡
編者按
當前,“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漢字英雄”、猜燈謎比賽、賽詩會等漢字漢語競賽節目不斷涌現,成為不少人茶余飯后的話題,這給了我們一種“漢語熱”的假象。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大學悄然把大學語文課從必修課降為選修,一些家長在孩子漢語還沒有說利索的情況下,就讓孩子沉浸在各種英語培訓和考試中,還有些滿腹學問的專家學者卻寫不好一篇深入淺出的文章。
當前,漢語語言學習被忽視,已經成為很多人關注的問題。那么,當前的漢語教育現狀怎樣?造成現狀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是什么?漢語教育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就此,我們采訪了著名語言學家、語文教育家、回族史學家、原《光明日報·語言文字》專刊主編張巨齡。
語言的人文性決定著它能訴諸人的精神層面
一般來說,語言有兩個性質,一是工具性,另一個是人文性。從歷史上來講,偏重于強調工具性,往往造成只把語文課當成一種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工具。人們很少談語言的人文性,或者說強調不夠,忽略了它對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精神層面的影響。
從工具性的角度來講,不管是哪個學科的學生,都離不開書寫。文章中每句話怎樣寫才得體?字與詞怎樣去鑲嵌才合適?這不是一年兩年就能純熟掌握的,甚至需要人們花一生時間去琢磨。
從人文性的角度來講,語言是訴諸人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在語言閱讀的過程中,會因為作者文章當中的各種形象、情節、技藝、糾葛、手法等,感動,甚至震撼人的心靈。比如說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作者筆下的韓麥爾先生雖然只是在教學生法語,但是我們從文章中讀到的卻是都德寫這篇文章時所傳達的愛國主義情感,是通過對母語的教學表現出來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大學里是沒有《大學語文》這門課的,后來在教育改革中做了填補,因為人們還是覺得,如果不學習我們祖國的語言文字,往往在學生的精神層面就有缺憾。從人文性的層面來看,語文這門課,決定著學生將來會成長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重理輕文的社會氛圍讓人缺乏人文氣息的涵養
人們常說,現在不少大學生少閱讀、少思考,很少能夠靜心研讀經典。有人認為,這些都是大學語文教育缺失的表現之一。我認為,語文教育缺失是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方面。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包括現在有的高校把《大學語文》從必修課降為選修課在內,人們對語言的學習逐漸忽視,很大程度上,都是與我們的社會大氛圍有關的。
從歷史上來講,其實我們的國家是“重文輕理”的,比如從老子、孔子、孟子,所謂儒、墨、道、法。鴉片戰爭之后,封建國家的門戶被西方國家打開,民族受到了欺凌,才逐漸感覺到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五四運動時期,提出要打倒舊文化,宣揚新文化,民主和科學的重要性才真正顯現出來。
實際上,在尚科學、尚技術的過程中,重文的這一優勢我們并不應該舍棄,既要有發達的人文科學,又要有先進的自然科學。但是歷史的發展卻恰恰相反,我們本該是一個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的國家,文理的發展應該是并駕齊驅的,但卻被新事物掩蓋住了舊事物,結果現在就變成“重理輕文”,也就造成了這方面的扭曲現象。
而細化到“文”的范疇內,也存在問題,那就是重文學、輕語言;在語言里還有新問題,重語言研究、輕語言教學。語言的這樣一個錯位的發展軌跡,不僅讓學生,也讓高校和教育改革者受到這個趨勢的影響,沒有認識到我們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國。所謂五千年文化里不僅有科學技術方面的四大發明,更多的是深厚的人文底蘊,這才是歷史積淀的落點。
所以說,現在談學生缺乏人文氣息,重點不應只放在學生學不學習語文上,而是必須要同時摒棄那種重理輕文的社會風氣,這不完全是一個學校應該考慮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應該警醒的。
除了重理輕文的歷史原因,學生缺乏人文素養,還與社會浮躁的氛圍有關。我們經常聽到,論文可以抄襲,考試甚至可以代筆,文章可以拿錢發表等等,這些就造成了一個相當惡劣的社會氛圍。
與浮躁的社會氛圍相對,學文卻是需要有堅強意志的,這與學習理科的狀態完全不同。通常文科的學習見效很慢,有些理科的學習卻是立竿見影的,再高明的老師一天也無法教出馬上能寫出好文章的學生,文字的技藝要練到純熟,不是一天的工夫,這就考驗著學習者的攻堅意識。
一些高校把大學語文作為一種選修課來處理,我覺得是不適當的,英語是必修,漢語是選修,無形之中自覺不自覺地就讓學生對祖國的語言和外語形成了一種心理落差,無疑就降低了祖國語言文字的地位,影響學生對語言和祖國的情感,長期來說,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有負面影響。
研究語言教學是語言工作者分內事
如今的大學語文教學普遍存在著課時少,沒有專門的語文教研室,經費少,教師發展空間小等掣肘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仍然離不開上面說到的重理輕文和浮躁的社會氛圍。然而,這些語言教學上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早在50多年前,呂叔湘先生就寫過一篇文章——《語言工作者當前的任務》。在這篇文章里,他就批評了大學不設語言教研室的問題,并且強烈呼吁學校應該重視語文教學。
長期以來,除了社會氛圍的問題,語文課之所以在大學里不受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教材和教師有關系。一個學科的設置要有教材作為藍本,要有專門的人才來從事教學,還要有學生來聽,教材、教師、學生,都是要不斷完善、改進和提高的。對于語文教學來講,呂叔湘先生曾提出,語文教學是語言工作者分內的事,我們的語言工作者必須關心教學工作者,要通過我們的研究,讓教學工作者體會到如何才能把教學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現實中的狀況卻往往是,語言研究者并不關心語言教學,只是在詞與詞之間玩文字游戲,研究“比一點差一點”該怎么說。而像呂叔湘先生、王力先生、葉圣陶先生等這些大語言學家和大文豪,都是關注基層語文教育的,不僅僅關心大學,也關心中小學。比如,葉圣陶先生不僅自己寫文章,他還給學生批改作文,從大學生到小學生都有。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語文教材,很多教材都沒有從大學教育的實際出發,因為大學是分科分系的,所以我們的語文教材也應該根據不同學科和不同領域進行設計。理科應該有理科的語文教材,比如可以講《水經注》,它的文章寫得很漂亮;如果想講科技方面的,可以從《天工開物》里面選文章,都可以根據不同學科精選出與學科相近的古代優秀的文章。這樣的教材既能讓學生學習語言,也有了專業的知識,讓語文教學與專業緊密相連,讓學生產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
再比如對于師范生的語文教材,也可以針對他們的專業進行特殊設計,教材中不妨編入一些語文教學的文章,或者一些教學小品,像小散文一樣,教會他們怎么去處理課堂上的突發事件,告訴他們上課的時候卡殼了怎么辦,學生提問提得很刁鉆該怎么辦,這些都是需要師范生學習的。所以我認為,對師范生的語文教材不妨放一些對他們做教師很有用的東西,告訴他們怎么教書,告訴他們什么是“教學機敏”,把語文教育與教學的應對能力結合起來。
對于學生來說,語文教育者不能讓學生覺得寫文章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如果教材和教師讓他們逐漸適應,并且從中嘗到了甜頭,興趣也就慢慢培養起來了,學生的意識也就逐漸轉變了。
有人問我,怎樣才能編出最適合的語文教材?實際上,再高明的編者也不會編出讓所有教師和學生都滿意的教材。語文教學一定是“三分書,七分講”,關鍵在于講,不僅僅是大學語文,基礎語文也是一樣,只有做到教師、教材、學生三者的良性互動,教師才能教得有水平,學生才能學得有興趣,語文課才能受歡迎,學校自然也就開始重視語文教學。這是一個系統的、自然運動的過程,其中當然也有我們當事人的主動性,要順應這個自然的系統運動,并且主動地去推動它,這樣的語文教學就會有所改善。
當然要提高語文教育的水平和提升其重要性,在教師、教材、學生良性互動的同時,更加需要的是整個教育部門,甚至社會對它的關注和重視,學校重視語文教學不夠,老師、語言工作者重視語文也不夠,需要通過上層來解決,現狀才能整體得到扭轉。
(光明網記者 吳晉娜采訪整理)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